

▲南京鼓樓醫院集團宿遷市人民醫院(簡稱老人民醫院)掛號區。該醫院在20年前從公立醫院變身為民營醫院。 (南方周末記者 張玥/圖)
眾多統計數據表明,二十年間,宿遷醫改將瀕臨垮掉的醫院救活過來,并緩解了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這幾年,宿遷的損失太大了。中央和江蘇省政府向各地下撥了很多項目、經費,用于建設標準化縣醫院、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但這些錢宿遷基本沒拿到。”
在公立醫院逐漸回歸的宿遷,不少民營醫院醫生開始考慮回到體制內。事業編制和退休收入是公立醫院最具誘惑力的優勢。
文 | 南方周末記者 張玥
一場激進式醫改,曾讓全國人民記住了宿遷這個地方。
2000年,宿遷開啟了被稱為“賣光醫院”式的改革,全市134家醫院中的133家變為民營。這種史無前例的做法,使宿遷成為全國醫療界用放大鏡去觀察的樣本。
宿遷地處江蘇省西北部,鄰近安徽和山東,人口五百余萬。迄今這里仍是一個窮地方,在2019年江蘇省13個省轄市中GDP總量排名墊底,僅為第一名蘇州的16%。
不過,《江蘇衛生計生年鑒》( 2019卷 )顯示,與蘇北五市乃至全省平均數據相比,宿遷醫療資源充裕,門診和住院價格最低。據江蘇省統計局公布數據,2018年宿遷市基本醫療衛生群眾滿意度位列全省第三。
時至今日,宿遷醫改已歷20年。但新的變化已開始出現,宿遷公立醫院有回潮之勢。
公立醫院為何回潮?醫院民營化是否解決了宿遷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如何評價宿遷醫改?
1
蓬勃十年
在宿遷,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仍舊認為,二十年前,“賣光醫院”是明智的選擇。
1990年代末,劉昆揚在沭陽的一個鄉鎮醫院工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形容,當時的宿遷是江蘇的經濟洼地,沭陽又是宿遷的洼地。財政倒掛,鄉鎮醫院發不出工資,基本處于倒閉狀態。
宿遷直到1996年才建市。當年39歲的仇和是市籌建領導小組成員,并任宿遷下轄的沭陽縣委書記。“賣光醫院”,就是從沭陽開始的。
2000年初,宿遷市政府出臺《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醫療衛生事業的意見》,提出放開社會辦醫準入,給予社會辦醫與公立醫院同等政策,土地可由政府劃撥,減免有關建設稅費。
改革的起點在沭陽。2000年3月,沭陽縣的3家鄉鎮衛生院進行改制試點。四年后,宿遷全市134家公立醫院中,133家完成民營化改制。
在劉昆揚看來,仇和是鐵腕官員,頂著極大阻力完成了這件事。當時很多買醫院的人是院領導和職工,“基本是半買半送,幾十萬就能買到一家鄉鎮醫院”。
曾經主持宿遷醫改的仇和,2006年升任江蘇省副省長,2007年轉任昆明市委書記,后升任云南省委副書記,但很快落馬。2016年,仇和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六個月,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200萬。
在宿遷,醫院的改制所得全部投入公共衛生防保體系。也就是說,宿遷政府把辦醫院的權力交給了民營,政府履行監督職能,同時承擔起了做好公共衛生的任務。
這場改革,在全國醫療界引起了極大爭論。
2006年,向來主張醫療衛生應由政府主導的北大李玲教授牽頭的課題組發表《宿遷醫改調研報告》,認為其并沒有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還引發了諸多新問題。同年12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者發表《宿遷醫療體制改革考察報告》,對宿遷醫改給予了積極評價。經濟學家周其仁也多次撰文評價宿遷醫改,認為其具有積極意義。
不論學者如何論戰,民營化之后,宿遷原本瀕臨倒閉的諸多醫院確實活了過來,還越做越好。
劉昆揚說,醫改后的第一個十年效果不錯。為了掙錢,老板們愿意在醫療上投入,鄉鎮醫院從平房變成了樓房,病房有了空調和衛生間。醫療設備和醫務人員的工資也得到了提高。
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得到了明顯扭轉。2003年以前,兩百萬人口的沭陽縣只有2臺CT機,改革后各鄉鎮醫院都配上了CT機。老百姓從看病一床難求,變得可以挑醫院看。2004年,只有初級職稱的劉昆揚,賬面工資已經比作為公辦小學校長的父親高許多。
在宏觀數據上,這個結論也得到了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對宿遷醫改的調研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宿遷市醫療資源增幅,在蘇北五市中處于最高水平,也顯著高于江蘇省平均增幅;另一方面,宿遷的均次門診費用和住院費用是蘇北五市中最低的,也顯著低于江蘇全省平均水平。
通過對蘇北五市新農合資金和社保資金的比照,他發現,沒有證據表明宿遷的民營醫院比其他地區的公立醫院存在更明顯的誘導需求行為。相反,其診療行為更規范,過度醫療現象更少見。

2
重回公立
宿遷醫改十年后,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這家公立醫院的出現,打破了宿遷民營醫療格局。
2011年開始,宿遷市政府決定按三級甲等醫院標準建設市第一人民醫院。在江蘇省衛健委網站上,可以看到2016年底的《江蘇省衛生廳擬批準設置“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公示書》,預計投資金額16.2億人民幣,床位2000張。
這所2016年7月建成的醫院是由宿遷市委、市政府投資興建的當時唯一一所大型綜合性公立醫院。
至于為什么重建公立醫院,采訪中,最多的說法是為了尋求財政補貼。
2003年SARS之后,政府加大了對公立醫療機構的直接補貼力度,但因為宿遷沒有公立醫院,拿不到這部分錢。
據國家衛健委主管的《健康報》2011年報道,一位宿遷市衛生局官員說,“這幾年,宿遷的損失太大了。中央和江蘇省政府向各地下撥了很多項目、經費,用于建設標準化縣醫院、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等,但這些錢宿遷基本沒拿到。”
在宿遷,一位民營醫院的經營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宿遷十年拿到的補貼,還沒有隔壁一年拿到的多。”
事實上,《江蘇省衛生計生統計年鑒》( 2019卷 )顯示,財政補助收入一欄,宿遷在江蘇13個市中墊底,其他城市補助從11億到80億不等,宿遷為8.9億,這還是第一人民醫院投入運營后的情況。
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建成僅僅是開始。2019年1月,《2019年宿遷市民生實事項目實施意見》專題發布會宣布,每個縣區將規劃建設1-2所公辦區域醫療衛生中心。多位受訪者表示,雖用詞復雜,但簡單來說,這就是建公立醫院。
在宿遷市衛健委2020年度預算中,來自財政撥款的收入增加1550萬元,用途之一就是區域醫療衛生中心建設項目經費的增加。相應地,衛生健康支出的增加部分主要仍在這一項目。
2020年6月26日,宿遷市沭陽縣衛健局發布一則醫院招聘公告稱,其下屬事業單位沭陽縣第一人民醫院、縣第二人民醫院和縣兒童醫院公開招聘工作人員90名,有正式事業編制。這三家醫院均隸屬于縣衛健局管理,是近期轉為公立的醫院。
其實在宿遷,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在診療上并無明顯差異。民營醫院也可以走醫保,與公立醫院花費差不多,環境和設施看不出明顯區別,人們更在意哪里醫生更好。遇到比較嚴重的病癥,他們則更信任徐州、南京的大醫院。
2020年8月25日和26日早上9點,南方周末記者分別來到宿遷兩家最大的綜合性醫院,南京鼓樓醫院集團宿遷市人民醫院( 簡稱老人民醫院 )和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前者是民營的,后者是公立的。
兩家醫院的大樓和設備都很新。工作日上午,老人民醫院的患者人數明顯更多。多位就醫者均表示,兩家醫院的收費差不多,老人民醫院在市中心,老醫生更多,所以人多。新人民醫院遠,年輕醫生多。“看病來講,沒什么差別。”
在一份市衛健委2020年的材料中可以看到,目前老人民醫院門急診128.5萬人次、住院6.5萬人次;第一人民醫院門急診63.8萬人次、住院4.5萬人次。
3
從挖專家、擴病床到“買病人”
在宿遷,對于當地醫療系統內部如何看待現狀,采訪十分困難,相關部門與醫生們大多緘口不言,甚至有醫生臨時爽約,說家人不讓聊。
一位民營醫院經營者對記者透露,“現在是宿遷民營醫院的寒冬。”與公立醫院相比,他們有著更多的經營壓力。
對民營醫院來說,首要問題就是人力成本高,骨干醫生價格高。挖一位專家,年薪動輒達到四五十萬。
曾經,宿遷民營醫院的藥費允許在政府采購價的基礎上上漲15%,而現在則被要求藥品“零差價”。對公立醫院來說,政府會有些補助。但民營醫院只能靠自己。
在稅收上,公立醫院因其非營利屬性而免交企業所得稅,營利性民營醫院則要交企業所得稅,即利潤的25%。
宿遷民營醫院的利潤究竟如何,可以在一些上市公司報表中找到答案。
金陵藥業( 000919.SZ )控股的宿遷市人民醫院( 即老人民醫院 ),是宿遷首家三甲醫院。2019財年,總資產12.43億,營業收入10.9億,凈利潤9078萬,凈利潤率8.3%。
復星醫藥( 600196.SH )持有宿遷市鐘吾醫院55%的股權。2019年一季度,鐘吾醫院總資產4.29億元,營收6761萬元,凈利潤406萬元,凈利潤率6%。
公告中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帶給民營醫院的好處。醫院無法用自己的樓和地抵押貸款,上市公司可以提供擔保。例如,2019年5月,復星醫藥為鐘吾醫院提供3000萬元的貸款擔保,該院的29名自然人股東則以自己的股份提供反擔保。
在宿遷,也有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倒閉的民營醫院。比較典型的是宿遷市珠江醫院,2014年投入3.5億新建,由于資金鏈斷裂,2015年停工。2017年,網上仍有這家醫院的項目轉讓信息,評論欄是民間投資者們呼喊還錢的聲音。
2020年8月,有網友為它拍攝視頻,醫院大樓仍然光鮮,但門口已種滿了青菜和黃豆,“投了那么多錢,一天都沒有運營。可惜了”。
從民營醫院發展的時間線來講,劉昆揚認為2010年左右是一個轉折點。
作為全國最早開展新農合試點的地區,沭陽縣2003年推廣新農合之后,有了國家報銷,老百姓敢看病了,于是需求量猛增,那時醫院大都賺到了錢。在宿遷,民營醫院經過申請,幾乎都能拿到醫保資格。
2010年以后,隨著醫院擴張,逐漸供過于求,產生了激烈的競爭。他計算,2000年左右,沭陽縣的床位不超過1200張,目前已有大約8000張。
病人總量的增長量低于醫院病床的擴張數,病房空置、醫保限費等因素,導致醫院利潤下降,于是出現了“買病人”的現象。劉昆揚解釋,買病人是指從村衛生室開始,向醫院推薦病人,每推薦一個就有回扣,層層向上級醫院推薦,則層層返點。
這個現象曾經是沒有的,是在當地不再“看病難”、病人開始挑醫院以后產生的。也有部分醫院提高收費標準以增加收入,但會導致病人流失。
劉昆揚形容,當醫院供大于求時,運轉困難的醫院不會迅速倒閉,“它會垂死掙扎的”,掙扎中就會產生各種違規亂象。
李一棋在宿遷從事醫療行業二十余年,也是一家醫院的股東。他證實眼下確實有“買病人”的情況,從上到下層層返點,二級醫院顯微外科拉病人最高能返診療費用的40%,一般病人提成10%,哪個醫生介紹就返給誰。一個碎石病人花費700元,醫生能提成500元。“大家都在搶病人。”
還出現了“套保”現象。比如醫院去跟養老院談,給院長回扣,讓老人們來住院,入院安排吃住,出院甚至還補貼生活費、送禮品。“老人們已經是‘大爺’,換著醫院住。對鄉鎮醫院來說,不‘套保’是無法生存的,很多醫院已經難以維持。”好多鄉鎮醫院都拉病人住院,有的住院不要錢,有的住院十天,自己出200元。
在鄉鎮醫院,真正的重病卻難以治療。醫保劃撥的費用不夠做手術,而且怕出事,如果發生了醫患糾紛,要醫院自己賠付。于是對于小醫院來說,只能是小病大治,大病向上推薦。
李一棋介紹,前兩年賣醫院賺到錢的人,主要是賺了房子的錢,蓋樓時便宜,現在增值了。早脫手的,可以賺錢,擴大規模的,反而危險。在醫保政策趨緊、公立醫院先后成立后,民營醫院逐漸沒人敢買了。“因為公立醫院一來,政策肯定不會向民營醫院傾斜的。大家是咬著牙撐下去。”
南方周末記者在宿遷走訪了兩家規模不小的民營醫院,它們近年來新建的大樓寬敞明亮,但病人不多。一家醫院的部分電梯停止運轉,另一家醫院則有相當一部分空間尚未開放。
4
事業編制的誘惑
在公立醫院逐漸回歸的宿遷,不少民營醫院醫生開始考慮回到體制內。李一棋介紹,自己的幾個醫生朋友都報考了新的公立醫院。
一位剛跳槽到公立醫院的當地醫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離職前,她所在的民營醫院有一種動蕩的氛圍,“一種大廈將傾的感覺”。
李羽渭是一位剛從宿遷離開的醫生。2010年左右,她研究生畢業,希望在醫院找到有事業編制的工作,但不容易。經同鄉介紹,來到了宿遷。宿遷的民營醫院歸衛生局管理,允諾有事業編制身份,待遇也照事業編制給。“當時覺得公立和民營沒有差別。”
唯一的不同,就是除了本科室外,還要兼顧醫院的其他工作。比如體檢、做120的初診和轉診以及去所在醫院新收購的鄉鎮醫院值班。
兩三年前,她離開宿遷,卻發現當初允諾的事業編制是沒有全國統一編碼的,外地公立醫院不認。社保斷檔五年,養老保險也只交了2012年以前的三年,甚至連檔案都是空白的。
這種情況,在當地離開的同事中多有發生。一位已離職的醫生給南方周末記者看養老保險記錄,工作十余年,養老保險僅繳納了2010-2012年的。近期申請勞動仲裁失敗,原因是“醫院正在與縣人社局機關保險處結算中,不存在不繳納養老保險問題”。
在李羽渭看來,民營醫院有優點,注重新技術發展,病房和設備都很新,而公立醫院上新項目、新設備,手續繁瑣,兩三年都拿不下來。對醫生來說,民營醫院也鼓勵發論文、做科研,補貼力度大,職稱晉升也更通暢。
跟劉昆揚一樣,她也認為2010年以前宿遷的民營醫院日子好過,但近十年效益逐漸跟不上,最近三年來,辭職的人開始變多,而且大多回到了公立醫院。
“這三年,政府開始改變策略,新建公立醫院,我們以前的身份是似是而非的,心里認為是事業單位編制,好多地方也認可,去銀行貸款也認為你是事業單位的人。但這三年,我們明白自己是徹徹底底的民營醫院了,心態就會變。以前我們知道可能缺社保,但相信政府早晚會補上,現在發現沒有指望了。”
醫生更多考慮的還是退休問題。事業單位和企業,退休收入相差三分之一左右。“在我們不認為自己是事業編制之后,感覺被拋棄了,編制對退休金影響太大了。”她的同事們也有跳槽去宿遷當地公立醫院的,收入雖然差不多,但心里踏實了。
劉昆揚說,不同的職業階段,醫生的訴求不同。年輕時,公立醫院保障好,病人多,能學的東西多。當業務成熟,可以獨當一面了,民營醫院工資更高。但到了五十歲左右,精力不如從前,可能被替代了,就覺得公立醫院更包容,退休待遇更好。
在待遇上,他形容民營醫院“明多暗少”,賬面工資高,但五險一金低,少繳甚至不繳養老保險和公積金;公立醫院“明少暗多”,工資之外,還有與事業單位人員相當的各項保險、公積金及福利收入,學歷或職稱高的還會有安家費、引進費用等補助。
在李一棋看來,相比醫生,更可憐的是護士。鄉鎮醫院的護士待遇非常低,月薪兩三千元。“小護士做個一兩年,都不愿意再干了,寧可去京東做客服。”
一位從公立醫院出來辦民營醫院的當地人士說,2000年初從公立醫院出來的人,宿遷有政策扶持,維持事業編制不變,后來就沒有了。“跟大領導很有關系,他支持你,就會給你政策,不支持你,以前的文件也沒有說作廢,但就是執行不了”。
南方周末記者在江蘇省衛健委網站看到,2014年宿遷市發文,對中心城區民營醫院的急需專業人才提供事業單位養老待遇,但門檻高,包括在該院連續工作十五年以上、足額繳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等條件。當地民營醫院受訪者普遍表示不知道這一文件。
專家朱恒鵬曾撰文分析,宿遷醫改不能歸因于仇和的強勢,他在昆明主政希望推動類似的改革,就推不動。因為活得滋潤的公立醫院,沒有動力改革。事業單位編制與否,退休待遇相差懸殊,公立醫院進行企業化改制,在編醫生一定激烈反對。這涉及我國養老金制度的改革。
即便如此,宿遷醫改從整體來看仍然成績斐然。眾多統計數據表明,二十年間,宿遷醫改將瀕臨垮掉的醫院救活過來,并緩解了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付明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從全省醫療數據來看,宿遷的門診費用、住院費用仍然是蘇州北部五市中最低的。同時,民營醫院主導的醫療體系,競爭公平和充分,使醫療資源的分布比較分散,沒有出現一家獨大的格局。
2020年,一份來自宿遷市衛健委的《宿遷市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情況介紹》提到,目前全市共有一級及以上醫院235所,較建市初期增加了78%;二級以上醫院43所,較建市時增加了4.4倍。全市醫療衛生資產211.41億元( 建市初期為4.95億元 ),其中醫療資產187.27億元( 超過淮安、連云港 )。據江蘇省統計局公布數據,2018年宿遷市基本醫療衛生群眾滿意度位列全省第三。
《江蘇衛生計生年鑒》( 2019卷 )也顯示,與蘇北五市乃至全省平均數據相比,作為GDP墊底的城市,宿遷醫療資源充裕,門診和住院價格最低。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劉昆揚、李一棋、李羽渭為化名。感謝創奇健康發展研究院執行理事長蔡江南對本文的幫助)

 雙創科技集市惠及大學校園創業學子
雙創科技集市惠及大學校園創業學子 黑龍江哈爾濱市發動各方力量迎戰暴風驟
黑龍江哈爾濱市發動各方力量迎戰暴風驟 “賣光醫院”20年后,宿遷發生了什么
“賣光醫院”20年后,宿遷發生了什么 河南省周口市電商扶貧造福百姓碩碩果累
河南省周口市電商扶貧造福百姓碩碩果累 四川華鎣:武術教育進校園
四川華鎣:武術教育進校園 2021年高考作文考什么?怎么考?抓住
2021年高考作文考什么?怎么考?抓住 山東國際糖酒會特設濟南館 展示泉城好味
山東國際糖酒會特設濟南館 展示泉城好味 “炮茶”繪就美麗鄉村
“炮茶”繪就美麗鄉村
 青島一對夫妻成拆遷網紅!手里9套房,開
青島一對夫妻成拆遷網紅!手里9套房,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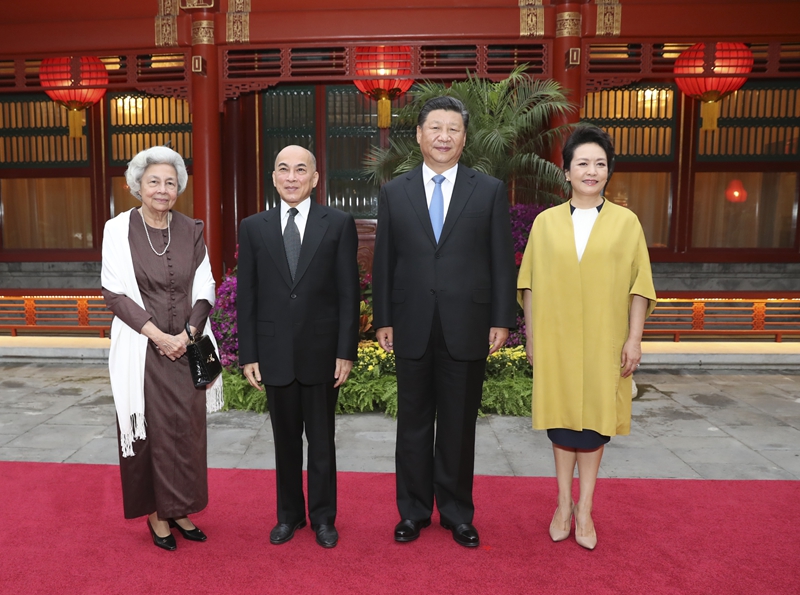 外交習語|這枚“友誼勛章”背后的故事
外交習語|這枚“友誼勛章”背后的故事 難得一見 采蓮湖社區鐵樹開花了
難得一見 采蓮湖社區鐵樹開花了 哥倫比亞慶祝麥德林花卉節 機器人擔任“
哥倫比亞慶祝麥德林花卉節 機器人擔任“ 2020年度天氣攝影師大賽獲獎作品欣賞
2020年度天氣攝影師大賽獲獎作品欣賞 東北邊城黑河迎來2020年第一場雪 快來感
東北邊城黑河迎來2020年第一場雪 快來感 北京秋葉爛漫 這才是秋天的顏色!
北京秋葉爛漫 這才是秋天的顏色! 濟南:淌豆寺千年古銀杏樹披金甲
濟南:淌豆寺千年古銀杏樹披金甲 喜看泉城騰巨龍 ——中鐵十四局集團一公
喜看泉城騰巨龍 ——中鐵十四局集團一公 濟南神秘的五七車站
濟南神秘的五七車站 “輪椅畫家”張海晶:畫筆繪出多彩脫貧
“輪椅畫家”張海晶:畫筆繪出多彩脫貧 一件紅色木雕 一段鮮活故事 山東郯
一件紅色木雕 一段鮮活故事 山東郯